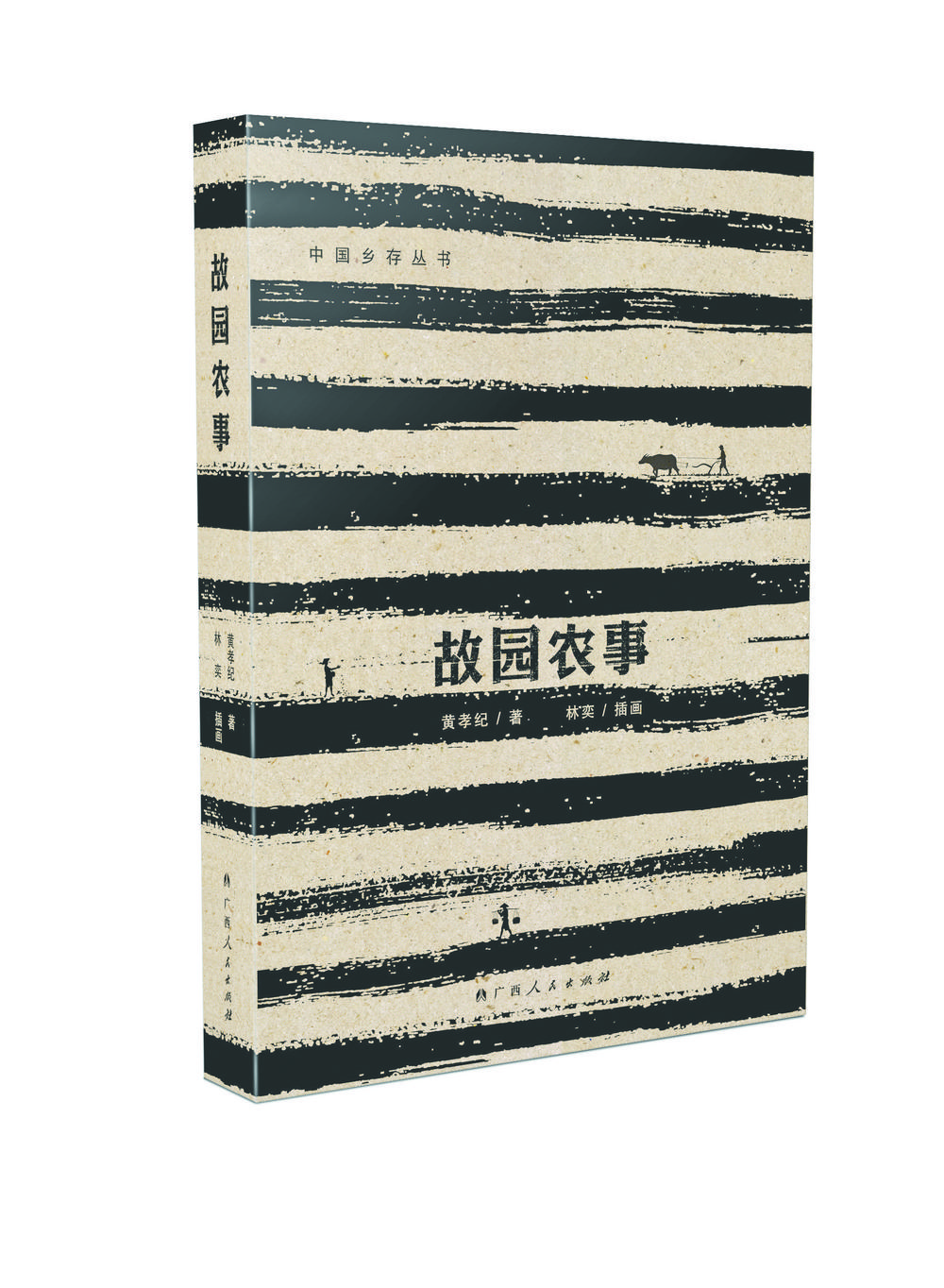◎黄孝纪 文/图
湘南是一个多山的地方。
我的故乡八公分村,就是在被群山围绕的偏僻一隅。那时候,故乡的山岭郁郁葱葱,故乡的江流碧波荡漾,故乡的田野土地肥沃,故乡的人们淳朴善良,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就是在这样一方水土度过的。
我们村庄地处永兴、桂阳、郴县(现为郴州市苏仙区)三县交界的区域,它坐西朝东,横亘在一列大致呈南北走向的山脉之下。村后紧挨着的那座山岭,俗称后龙山,据说关乎一村的风水,生长着高大而茂密的枞树、樟树、苦槠等品种繁多的树木,保持着原始的状态,禁止砍伐。青砖黑瓦的村旁,有诸多的古树,古枫、古椆、古柏、古樟,无不耸立云天,繁荫覆盖。村前便是江流和稻田。这条江流没有名字,其源头在上游山岭之间,曲曲折折流到我们村前时,江面已变得开阔而平缓,沿江两岸满是高大的树木,尤以苍柏、垂柳、梧桐、油桐居多,灌木、荆棘和野生小竹子也多,将江水染成翠绿。沿途的江上,筑有多道石坝,一段段的江水被拦截抬升,由长长的水圳引入江岸两边的稻田。对于我们村庄来说,即便再干旱的年份,农田的灌溉用水,基本上还是无虞的。江上架有石桥和木桥,连通两岸。而在江对岸的稻田之后,又是连绵起伏的山岭。长久以来,这条江蜿蜒流淌,哺育着两岸大小的村庄。
在传统农耕的故乡,种田无疑是最重要的农事。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分田到户之前,我的故乡与一江上下的上羊乌、下羊乌、土方头、油市塘、朽木溪、臼林同属于羊乌大队,这之中,我们村与上羊乌村是两个大的自然村,其余的都是小村。按照全大队统一的排序,我们村分成四个生产队,分别叫五队、六队、七队和八队,我家在五队。在我童年时期,生产队已种植双季稻,春种一季早稻,秋种一季晚稻。只是所种的还多是常规水稻,产量也并不很高,每个生产队一年稻田的产出,在上交公粮之后,分给各家的稻谷,尚不能解决乡人的温饱问题。
种田自然是辛苦的,杀叶积肥,犁田耙田,种秧莳田,管水治虫,乃至割禾晒谷,每一道农活,都需要付出无数的汗水。尤其是盛夏抢收早稻、抢插晚稻的“双抢”季节,烈日炎炎,劳动强度巨大,甚为辛劳。我也从小就参加农田里力所能及的劳动,在父母、姐姐和乡人的身体力行之下,耳濡目染学会了一些简单的农耕技能,培养了吃苦耐劳的精神。那个年代,乡村没有闲田,每一处能栽种的稻田,都要种上水稻。一年中,当江流两岸的稻田里,碧绿的禾苗渐渐变成金黄的稻浪,绵延着,从一个村庄扩展到另一个村庄,直到模糊的远山和远村,那真是令人喜悦的景象。分田到户的早期,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激发,加上杂交水稻的广泛种植,农药、化肥的使用,粮食产量显著提高,成就了多年的丰收盛况,也彻底解决了长期困扰乡村的温饱大事。
作土也是一项日常的农事。故乡的园土,散落在江两岸的山脚或山窝,曾有多年,红薯和小麦,是两种最主要的旱土作物,它们是除水稻之外的重要粮食。分田到户后,随着水稻的增产增收,小麦渐渐无人种植。红薯的种植依旧在延续,只是它那曾经担负着故乡人家“半年粮”的使命已然不再,成了酿造红薯烧酒的原料,此外加工红薯干、红薯粉,总之慢慢成了乡人日常饮食的辅助品。园土里的其他作物品种多样,因季节交替而轮作,花生、高粱、黄豆、蚕豆、辣椒、茄子、南瓜、苦瓜、白菜、萝卜、肥菜、风菜(方言)……应有尽有。对于乡人来说,这些来自园土的收获,自给自足,既保证了家中一日三餐的菜蔬,还可拿出一些喂猪,有些物产还能在赶圩日卖点钱,贴补家用。
相比水田和旱土,故乡的山岭更多。这些绵延的山岭,以红壤土质居多,主要种植油茶。油茶林里,也间杂着杉树、油桐树、山苍子树等经济林木。长期以来,育山护林既是乡人约定俗成的准则,也是重要的农事。在生产队时期,一年的冬春两季,当稻田和园土里的主要农事忙完以后,乡人就会到油茶岭上垦山。垦过山的油茶林,长得愈发高大而茂密,开花多,结果大。记得山岭分到户之后,我的老父亲长年里一有闲暇,就去村前对门岭上那片自家的油茶山垦山护林。丰收的年景,我们家的这片油茶林,能摘六七十担油茶果,可榨几百斤金黄芳香的新茶油。油茶山上,也是我们平日里捡柴的地方,那时乡村的砖灶,以烧柴火为主,只有在寒冬腊月,才会烧炭。山间也多生长野竹子,以及金樱子、黄栀子、香薷等野生药用植物,在扯竹笋、采药草的时节,常见乡人忙碌的身影。
昔日炊烟袅袅的故乡,鸡鸣犬吠,充满了生机。养殖家禽家畜,是故乡人家的传统。在生产队时期,耕牛是集体的重大财产,也是耕田最主要的畜力,通常由各生产队安排专人牧放。那些牛铃叮当、早出晚归的放牛场景,是每天都要上演的乡村经典画面。那时差不多家家户户都养猪,养大的肥猪,由生产队安排上交公社食品站,完成国家收购任务,或在过节过年时宰杀分肉,相应地,生产队则会按猪的重量给农户计算应得的工分,这样的养猪方式,乡人俗称养工分猪。养鸡、鸭、鹅的人家也多,这些活泼可爱的家禽,每天散布在乡村的各个角落,觅食或者嬉闹。村前的池塘众多,大大小小,一个连着一个,碧波荡漾。池塘里养着鱼,池面常有鹅鸭浮游,不时也有水牛冲进去躺着,舒舒服服地泡水。干塘的日子,塘岸塘里,观看的、捉鱼的,人头攒动,笑逐颜开,是乡村欢乐的时光。分田到户后,养牛、养猪的人家曾一度热情高涨,也实实在在给农家带来了不少收入。只是随着时代的演进,多年之后,耕牛和猪都从故乡消失了,令人唏嘘。
在漫长的岁月里,农耕的故乡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除了耕种和养殖,乡人挣钱的门路很少。亦因此,到了长冬,差不多就进入了农闲期。不过有手艺的乡村工匠,在农闲的好几个月里,倒正是出门赚钱的时候。那时的故乡,离不开木匠、漆匠、石匠、砖瓦匠、铁匠、补锅匠、补鞋匠、弹棉匠、裁缝……他们以自己勤勉的劳动,维系着乡村手艺的新陈代谢。而身无长技的乡人们,则拿些小的本钱,凭着一身力气和耐劳的品格,常成群结伴,走几十里山路,深入邻县的林区购买杉木背回家,再趁着赶圩的日子,背到十里外的圩场上卖掉,赚取几角几元的辛苦钱。
农闲也是乡村兴修水利和各项大型建设的大好时机。村前江上的石坝,稻田间那一条条修长的水圳,村旁那俗称山塘的小水库,都是一辈辈的乡人,用无数的劳动和汗水建成的。我的童年见证了那个全民修水库的时代的尾巴,我跟随送饭的母亲到邻村水库工地上所见到的热烈劳动场面,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我也目睹了山脚下那条简易黄土公路的修筑和通车,见证了乡人抬水泥电杆建设进村电网的情景。这条公路和电网,从此将闭塞的故乡与外界,与快速发展的时代,更紧密地联系了起来。乡人点油灯的日子,成为过往。讲古、看戏的传统乡村娱乐形式,也被看电影、电视所取代。农业的丰收,经济的发展,也促成了故乡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建房热潮,每年冬闲,一栋栋新瓦房拔地而起。原先那个仿佛凝固的浓墨般的青砖黑瓦的村庄,迅速洇染开来。
我很庆幸,我的童年和少年能在湘南山区的这一方土地上度过。童年的故乡,人们专务于农耕,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平静简朴的田园生活。年少时,欣逢革故鼎新的时代,生产队解体,田土山包产到户,这时的乡人更焕发出了对农事的热情,热爱田园,勤恳奋发,朝气蓬勃,如今看来,这也是我半百人生所见的故乡农业的繁盛期。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故乡农人,离开了农村,脱离了农事,他们的身影游动在城镇的建筑工地,或定格在工厂的流水线上。年老的农民,则带着一辈子积攒下来的农耕经验,带着对田园荒芜的痛惜和无力,渐渐离开尘世。浩荡潮流之下,村庄变得冷落,乡人纷纷弃耕,田园多有荒芜。猪儿拱土,牛儿春耕,日渐稀疏,不复往年。长久以来维系着故乡世代绵延的传统农耕,在与新兴工业文明的交锋之中,显得不堪一击。
作为一个拥有着数千年农耕文明的古国,农事,原是天人之间最原始的角力,也是人与这个世界最直接、最质朴的交流方式。千百年来,农人依靠土地划分自己的“疆界”和“王国”,在这片土地上,用自己的耙子和犁,耕耘着土地,灌溉着土地,以自己最为独特、最原始的方式参与着世界的造化和运转,改变着大地的纹理和气象;民俗、道德、伦理……因之得以形成,古老的文明得以无尽延续。农事,让土地呈现如一块永不枯竭、日新又新的画卷,它是农人的尊严与骄傲。
传统农耕,也成就了天人间最美好的和谐。土地,是上天的馈赠,而农事,则是人与天地所能发生的最为亲密的关系,它让人们与自然朝夕相处,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在这里亲近山川河流,在这里感受阳光雨露,在这里感受天地神人的神秘交汇……来自土地深处的与人连为一体的力量,让一代代农人将毕生贡献于它,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最后,化作尘土融于斯。
今天,当我们乘坐飞机缓缓升入云端,从空中俯视大地,我们仍能看见,那些深刻改变人类版图和历史走向的手笔:那开荒凿山留下的巨大豁口;那汩汩流淌的不竭运河;而那稻谷映出的片片金黄,在阳光下闪耀,迷醉了我们的双眼……
它们是人类的杰作,农人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大地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