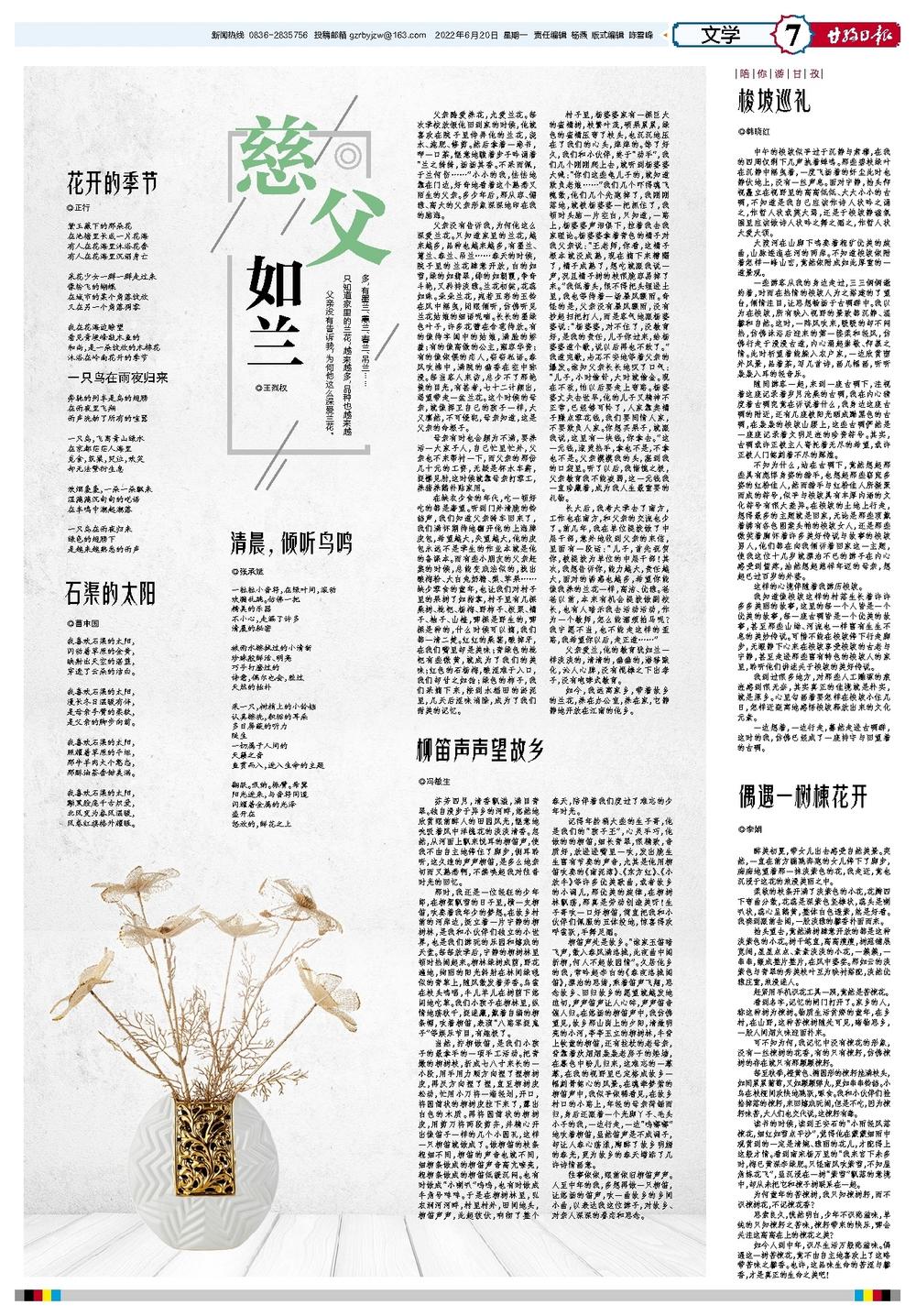◎王烈权
父亲没有告诉我,为何他这么深爱兰花。只知道家里的兰花,越来越多,品种也越来越多,有墨兰、蕙兰、春兰、吊兰……
父亲酷爱养花,尤爱兰花。每次学校放假他回到家的时候,他就喜欢在院子里侍弄他的兰花,浇水、施肥、修剪。然后拿着一卷书,呷一口茶,惬意地踱着步子吟诵着“兰之猗猗,扬扬其香。不采而佩,于兰何伤……”小小的我,怯怯地靠在门边,好奇地看着这个熟悉又陌生的父亲。多少年后,那从容、儒雅、高大的父亲形象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
父亲没有告诉我,为何他这么深爱兰花。只知道家里的兰花,越来越多,品种也越来越多,有墨兰、蕙兰、春兰、吊兰……春天的时候,院子里的兰花肆意开放,白的如雪,绿的如翡翠,绯的如朝霞,争奇斗艳,又矜持淡雅。兰花初绽,花蕊如珠。朵朵兰花,宛若五彩的玉铃在风中摇曳,闭眼倾听,仿佛听见兰花姑娘的细语呢喃。长长的墨绿色叶子,许多花蕾在含苞待放。有的像待字闺中的姑娘,满脸的娇羞;有的像高傲的公主,雍容华贵;有的像依偎的恋人,窃窃私语。春风吹拂中,满院的幽香在空中弥漫。每当客人来访,总少不了那艳羡的目光,有甚者,七十二计频出,渴望带走一盆兰花。这个时候的母亲,就像捍卫自己的孩子一样,大义凛然,不可侵犯,母亲知道,这是父亲的命根子。
母亲有时也会颇为不满,要养活一大家子人,自己忙里忙外,父亲也不来帮衬一下,而父亲的那份几十元的工资,无疑是杯水车薪,捉襟见肘,这时候就靠母亲打零工,养猪养鹅补贴家用。
在缺衣少食的年代,吃一顿好吃的都是奢望。听到门外清脆的铃铛声,我们知道父亲骑车回来了,我们满怀期待地翻开他的上海牌皮包,希望越大,失望越大,他的皮包永远不是学生的作业本就是他的备课本。而有些小朋友的父亲赶集的时候,总能变戏法似的,找出酸梅粉、大白兔奶糖、梨、苹果……缺少零食的童年,也让我们对村子里的果树了如指掌,村子里有几棵桑树、枇杷、杨梅、野柿子、板栗、橘子、柚子、山楂,哪棵是野生的,哪棵是种的,什么时候可以摘,我们都一清二楚。红红的桑葚,酸掉牙,在我们嘴里却是美味;青绿色的枇杷有些微黄,就成为了我们的美味;红色的石杨梅,酸涩难于入口,我们却甘之如饴;绿色的柿子,我们采摘下来,按到水稻田的淤泥里,几天后涩味消除,成为了我们甜美的记忆。
村子里,杨婆婆家有一棵巨大的蜜橘树,枝繁叶茂,硕果累累,绿色的蜜橘压弯了枝头,也沉沉地压在了我们的心头,痒痒的。馋了好久,我们和小伙伴,终于“动手”,我们几个刚刚爬上去,就听到杨婆婆大喊:“你们这些龟儿子的,就知道欺负老娘……”我们几个吓得魂飞魄散,他们几个先跑掉了,我刚刚落地,就被杨婆婆一把抓住了,我顿时头脑一片空白,只知道,一路上,杨婆婆声泪俱下,拉着我去我家理论。杨婆婆拿着青色的橘子对我父亲说:“王老师,你看,这橘子根本就没成熟,现在摘下来糟蹋了,橘子成熟了,想吃就跟我说一声,况且橘子树的枝很脆容易掉了来。”我低着头,恨不得把头埋进土里,我也等待着一场暴风骤雨。奇怪的是,父亲没有暴风骤雨,没有抄起扫把打人,而是客气地跟杨婆婆说:“杨婆婆,对不住了,没教育好,是我的责任,儿子你过来,给杨婆婆道个歉,说以后再也不敢了。”我道完歉,忐忑不安地等着父亲的爆发。谁知父亲长长地叹了口气:“儿子,小时偷针,大时就偷金。现在不改,怕以后要走上弯路。杨婆婆丈夫去世早,他的儿子又精神不正常,已经够可怜了,人家靠卖橘子赚点零花钱,我们要同情人家,不要欺负人家。你想买果子,就跟我说,这里有一块钱,你拿去。”这一元钱,滚烫热手,拿也不是,不拿也不是。父亲摸摸我的头,塞到我的口袋里。听了以后,我惭愧之极,父亲教育我不能凌弱,这一元钱我一直珍藏着,成为我人生最重要的礼物。
长大后,我考大学去了南方,工作也在南方,和父亲的交流也少了。前几年,我在单位提拔做了中层干部,意外地收到父亲的来信,里面有一段话:“儿子,首先祝贺你,被提拔为单位的中层干部!其次,我想告诉你,能力越大,责任越大,面对的诱惑也越多,希望你能像我养的兰花一样,高洁、优雅。爸爸以前,本来有机会提拔做副校长,也有人暗示我去活动活动,作为一个教师,怎么能溜须拍马呢?我宁愿不当,也不能走这样的歪路,我希望你以后,走正道……”
父亲爱兰,他的教育犹如兰一样淡淡的,清清的,幽幽的,潜移默化,沁人心脾,没有棍棒之下出孝子,没有咆哮式教育。
如今,我远离家乡,带着故乡的兰花,养在办公室,养在家,它静静地开放在江南的他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