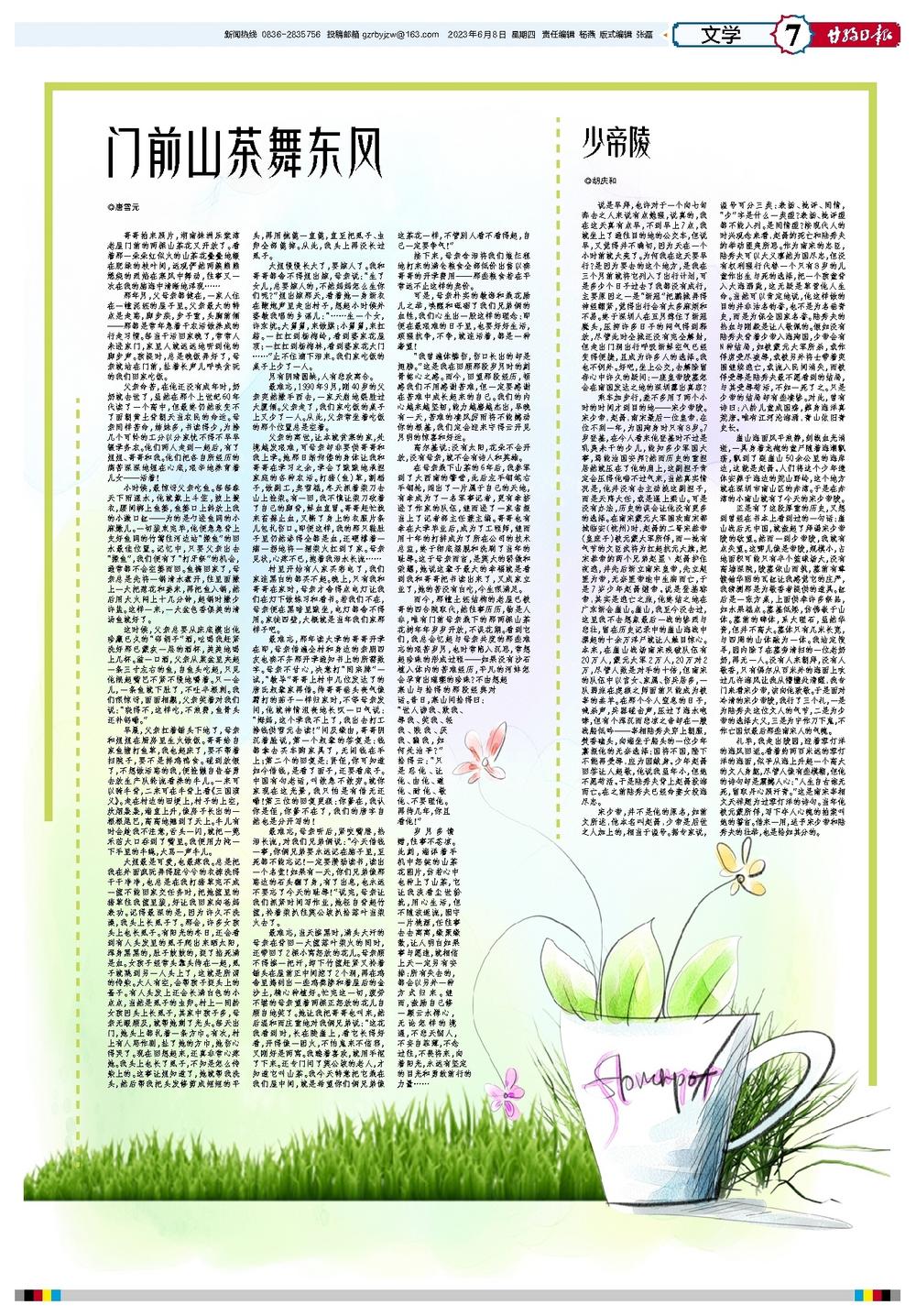◎胡庆和
说是早拜,也许对于一个向七旬奔去之人来说有点勉强,说真的,我在这天真有点早,不到早上7点,我就坐上了通往目的地的公交车,但说早,又觉得并不确切,因为天在一个小时前就大亮了。为何我在这天要早行?是因为要去的这个地方,是我在三个月前就将它列入了出行计划,可是多少个日子过去了我都没有成行,主要原因之一是“新冠”把鹏城弄得神经绷紧,觉得出行会有太多麻烦和不易。终于深圳人在五月缚住了新冠魔头,压抑许多日子的闷气得到释放,尽管此时全城还没有完全解封,但走出门洞出行呼吸新鲜空气已经变得便捷,且成为许多人的选择。我也不例外。好吧,坐上公交,去解除留存心中许久的疑问:一座皇帝陵墓怎会在南国发达之地的深圳露出真容?
乘车加步行,差不多用了两个小时的时间才到目的地——宋少帝陵。宋少帝,赵昺,南宋最后一位皇帝,在位不到一年,为国殉身时只有8岁。7岁登基,在今人看来他登基时不过是乳臭未干的少儿,能知多少军国大事,焉能治国安邦?然而历史的重担居然就压在了他的肩上,这副担子肯定会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当然真实情况是,他并没有去主动挑这副担子,而是天降大任,或是逼上梁山。可是没有办法,历史的误会让他没有更多的选择。在南宋蒙元大军围攻南宋都城临安(杭州)时,赵昺的二哥宋恭帝(皇庶子)被元蒙大军所俘,而一批有气节的文臣武将为扛起抗元大旗,把宋恭帝的两个兄弟赵昰丶赵昺护住夜逃,并先后新立南宋皇帝,先立赵罡为帝,无奈罡帝途中生病而亡,于是7岁少年赵昺继帝。说是登基称帝,其实是逃亡之旅,他终结之地在广东新会崖山。崖山,我至今没去过,这里我不去想象最后一战的惨烈与悲壮,留在历史记录中的崖山海战中漂起的十余万浮尸就让人触目惊心。本来,在崖山战场南宋残破队伍有20万人,蒙元大军2万人,20万对2万,尽管人数是对手的十倍,但南宋的队伍中以宫女、家属、伤兵居多,一队弱旅在虎狼之师面前只能成为被宰的羔羊。在那个令人窒息的日子,喊杀声,兵器碰击声,压过了海水咆哮,但有个浑沉而悲凉之音却在一艘战船低吟——宰相陆秀夫穿上朝服,焚香磕头,向端坐于船头的一位少年禀报他的无奈选择:国将不国,陛下不能再受辱,应为国献身。少年赵昺回答让人起敬,他说我虽年小,但绝不愿苟活。于是陆秀夫背上赵昺投海而亡。在之前陆秀夫已经命妻女投海尽忠。
宋少帝,并不是他的原名,如前文所述,他本名叫赵昺,少帝是后世之人加上的,相当于谥号。据专家说,谥号可分三类:表扬、批评、同情,“少”字是什么一类型?表扬、批评型都不能入列。是同情型?按现代人的时兴观念来看,赵昺的死亡和陆秀夫的举动匪夷所思。作为南宋的忠臣,陆秀夫可以大义凛然为国尽忠,但没有权利强行代替一个只有8岁的儿童作出生与死的选择,把一个孩童背入大海溺毙,这无疑是草菅他人生命。当然可以肯定地说,他这样做的目的并非沽名钓誉,也不是为名垂青史,而是为保全国家名誉。陆秀夫的热血与刚毅是让人敬佩的。假如没有陆秀夫背着少帝入海殉国,少帝会有N种结局,如被蒙元大军所杀,或作俘虏受尽凌辱,或被另外将士带着突围继续逃亡,或流入民间消失,而被俘受辱是陆秀夫最不愿看到的结局,与其受辱苟活,不如一死了之。只是少帝的结局却有些凄惨。对此,曾有诗曰:八龄儿童成国殇,葬身海洋真荒唐。唯有江河沦海涌,青山依旧青史长。
崖山海面风平浪静,剑戟血光消逝,一具身着龙袍的童尸随着海潮飘荡,飘到了距崖山50余公里的海岸边,这就是赵昺。人们将这个少年遗体安葬于海边的荒山野岭,这个地方就在深圳市南山区的赤湾。于是在赤湾的小南山就有了今天的宋少帝陵。
正是有了这段厚重的历史,又想到曾经在书本上看到过的一句话:崖山战后无中国,就激起了拜谒宋少帝陵的欲望。然而一到少帝陵,我就有点失望。这哪儿像是帝陵,规模小,占地面积可能只有半个篮球场大,没有高墙深院,陵墓依山而筑,墓前有尊镀铀华丽的瓦缸让我感觉它的庄严,我猜测那是为敬香者提供的道具。缸后是一张方桌,上面供奉许多祭品,如水果糕点。墓基低矮,仿佛嵌于山体。墓前的碑体,系大理石,虽然华贵,但并不高大。墓体只有几米长宽,与四周的山体融为一体。我站定搜寻,园内除了在墓旁清扫的一位老奶奶,再无一人。没有人来朝拜,没有人敬香,只有偶尔从百米外的海面上吹过几许海风让我从懵懂处清醒,我专门来看宋少帝,该向他致敬。于是面对冷清的宋少帝陵,我行了三个礼,一是为陆秀夫这位文人的气节,二是为少帝的选择大义,三是为宁作刀下鬼,不作亡国奴最后那些南宋人的气魄。
礼毕,我走出陵园,迎着零仃洋的海风回返。看着约两百米远的零仃洋的海面,似乎从海上升起一个高大的文人身躯,尽管人像有些模糊,但他的诗句却是震撼人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南宋宰相文天祥题为过零仃洋的诗句。当年他被元蒙所俘,写下夺人心魄的拍案叫绝的誓言。借来一用,送予宋少帝和陆秀夫的壮举,也是恰如其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