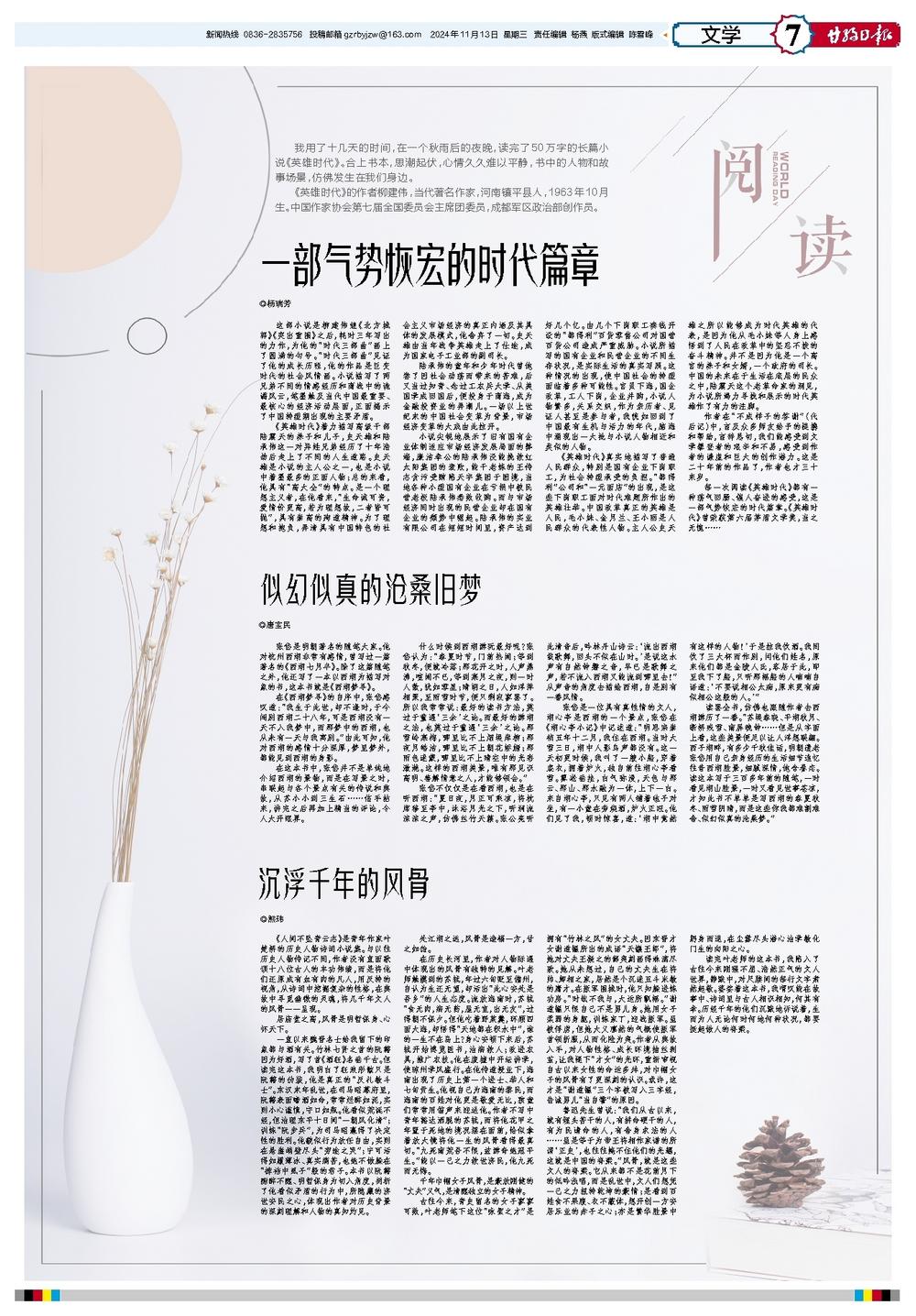◎熊玮
《人间不坠青云志》是青年作家叶楚桥的历史人物诗词小说集。与以往历史人物传记不同,作者没有直面歌颂十八位古人的丰功伟绩,而是将他们还原成有血有肉的凡人,用反转的视角,从诗词中挖掘复杂的性格,在典故中寻觅幽微的灵魂,将几千年文人的风骨一一呈现。
居庙堂之高,风骨是明哲保身、心怀天下。
一直以来魏晋名士给我留下的印象都与酒有关。竹林七贤之首的阮籍因为好酒,写了首《酒狂》名垂千古。但读完这本书,我明白了狂浪形骸只是阮籍的伪装,他是真正的“反礼教斗士”。东汉末年乱世,在司马昭幕府里,阮籍表面嗜酒如命,常常烂醉如泥,实则小心谨慎,守口如瓶。他看似荒诞不经,但治理东平十日间“一朝风化清”;训练“阮步兵”,为司马昭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他貌似行为放任自由,实则在悬崖峭壁尽头“穷途之哭”;宁可活得如履薄冰、真实痛苦,也绝不做躲在“裤裆中虱子”般的君子。本书以阮籍酣醉不醒、明哲保身为切入角度,剖析了他看似矛盾的行为中,所隐藏的济世安民之心,体现出作者对历史背景的深刻理解和人物的真知灼见。
处江湖之远,风骨是造福一方,甘之如饴。
在历史长河里,作者对人物际遇中体现出的风骨有独特的见解。叶老师触摸到的苏轼,年过六旬贬至儋州,自认为生还无望,却活出“此心安处是吾乡”的人生态度。流放海南时,苏轼“食无肉,病无药,屋无室,出无友”,过得朝不保夕。但他吃着野菜羹,环顾四面大海,却悟得“天地都在积水中”,谁的一生不在岛上?身心安顿下来后,苏轼开始博览医书,治病救人;改进农具,推广农技。他在废墟中开坛讲学,使琼州学风盛行。在他传道授业下,海南出现了历史上第一个进士、举人和七旬贡生。他视自己为海南的黎民,而海南的百姓对他更是敬爱无比,孩童们常常用笛声来迎送他。作者不写中青年豁达洒脱的苏轼,而将他花甲之年置于死地的境况摆在面前,恰似拿着放大镜将他一生的风骨看得最真切。“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能以一己之力救世济民,他九死而无悔。
千年巾帼女子风骨,是豪放刚健的“丈夫”义气,是清醒独立的女子精神。
古往今来,青史留名的女子寥寥可数,叶老师笔下这位“咏絮之才”是拥有“竹林之风”的女丈夫。因东晋才女谢道韫所出的成语“天镶王郎”,将她对丈夫王凝之的鄙夷刻画得淋漓尽致。她从未想过,自己的丈夫生在将帅、卿相之家,居然是个沉迷五斗米教的庸才。在叛军围城时,他只知躲进练功房。“时哉不我与,大运所飘摇。”谢道韫只恨自己不是男儿身。她用女子柔弱的身躯,训练家丁,迎战叛军。虽被俘虏,但她大义凛然的气概使叛军首领折服,从而化险为夷。作者从典故入手,对人物性格、成长环境抽丝剥茧,让我褪下“才女”的光环,重新审视自古以来女性的命运多舛,对巾帼女子的风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或许,这才是“谢道韫”三个字被写入三字经,告诫男儿“当自警”的原因。
鲁迅先生曾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风骨,就是这些文人的脊梁。它从来都不是花前月下的低吟浅唱,而是乱世中,文人们想凭一己之力扭转乾坤的豪情;是看到百姓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想开创一方安居乐业的赤子之心;亦是繁华胜景中躬身而退,在尘嚣尽头潜心治学教化门生的向阳之心。
读完叶老师的这本书,我陷入了古往今来刚强不屈、浩然正气的文人世界,静默中,对尺牍间的每行文字肃然起敬。婆娑着这本书,我喟叹能在故事中、诗词里与古人相识相知,何其有幸。历经千年的他们沉默地诉说着,生而为人无论何时何地何种状况,都要挺起做人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