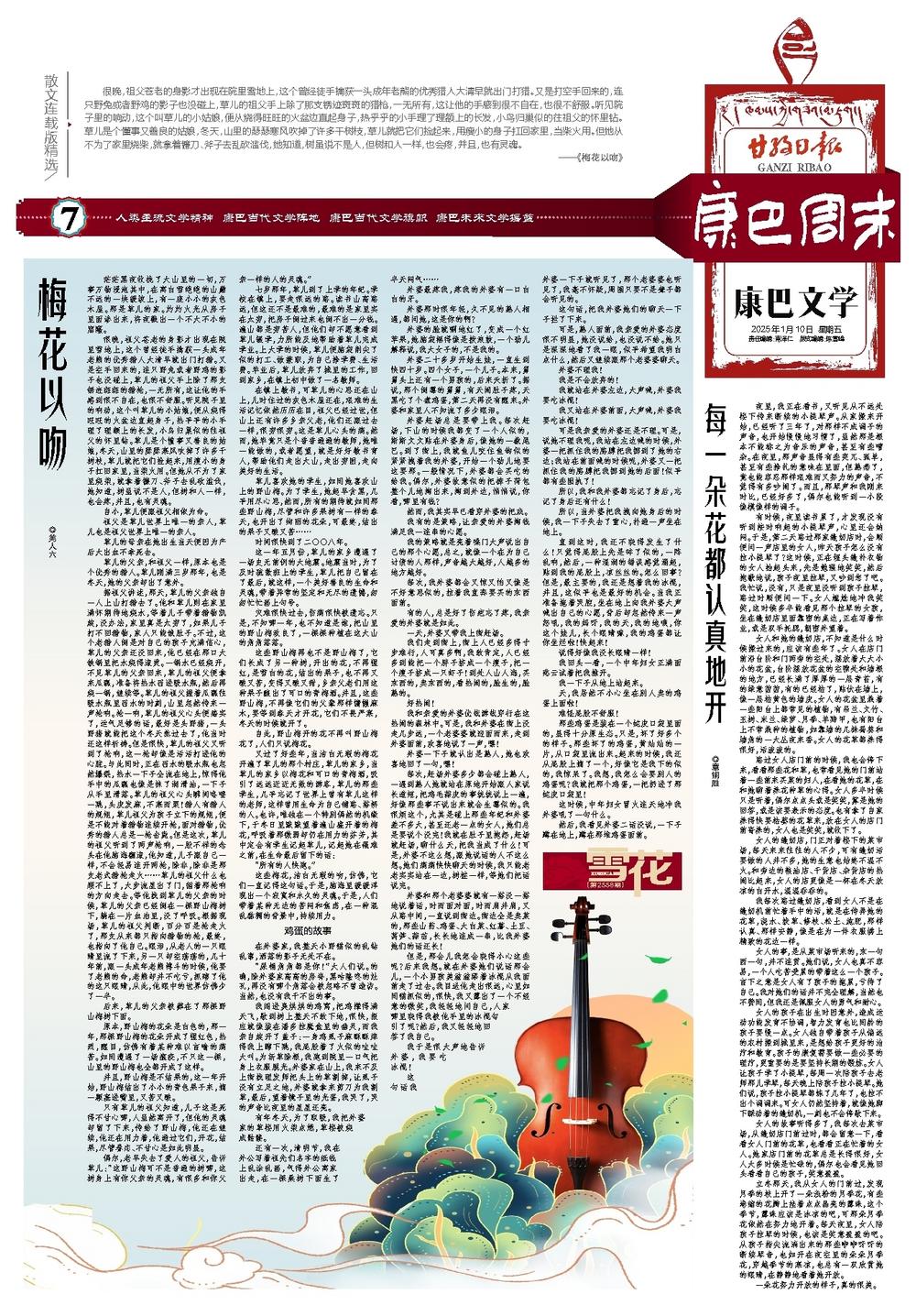◎羌人六
茫茫黑夜收拢了大山里的一切,万事万物浸泡其中,在离白雪皑皑的山巅不远的一块缓坡上,有一座小小的灰色木屋。那是草儿的家。灼灼火光从房子里面渗出来,将夜戳出一个不大不小的窟窿。
很晚,祖父苍老的身影才出现在院里雪地上,这个曾经徒手擒获一头成年老熊的优秀猎人大清早就出门打猎。又是空手回来的,连只野兔或者野鸡的影子也没碰上,草儿的祖父手上除了那支锈迹斑斑的猎枪,一无所有,这让他的手感到很不自在,也很不舒服。听见院子里的响动,这个叫草儿的小姑娘,便从烧得旺旺的火盆边直起身子,热乎乎的小手理了理额上的长发,小鸟归巢似的往祖父的怀里钻。草儿是个懂事又善良的姑娘,冬天,山里的瑟瑟寒风吹掉了许多干树枝,草儿就把它们捡起来,用瘦小的身子扛回家里,当柴火用。但她从不为了家里烧柴,就拿着镰刀、斧子去乱砍滥伐,她知道,树虽说不是人,但树和人一样,也会疼,并且,也有灵魂。
自小,草儿便跟祖父相依为命。
祖父是草儿世界上唯一的亲人,草儿也是祖父世界上唯一的亲人。
草儿的母亲在她出生当天便因为产后大出血不幸死去。
草儿的父亲,和祖父一样,原本也是个优秀的猎人。草儿刚满三岁那年,也是冬天,她的父亲却出了意外。
据祖父讲述,那天,草儿的父亲独自一人上山打猎去了。他和草儿则在家里满怀期待地烧水,等着儿子带着猎物凯旋,没办法,家里真是太穷了,如果儿子打不回猎物,家人只能饿肚子。不过,这个老猎人倒是对自己的孩子充满信心,草儿的父亲还没回来,他已经在那口大铁锅里把水烧得滚烫。一锅水已经烧开,不见草儿的父亲回来,草儿的祖父便拿来瓜瓢,准备将热水舀进暖水瓶,然后再烧一锅,继续等。草儿的祖父握着瓜瓢往暖水瓶里舀水的时刻,山里忽然传来一声枪响。枪一响,草儿的祖父心头便踏实了,运气足够的话,最好是头野猪,一头野猪就能把这个冬天熬过去了,他当时还这样祈祷。但是很快,草儿的祖父又听到了枪响,这一枪却像是活活打进他的心脏。与此同时,正在舀水的暖水瓶也忽然爆裂,热水一下子全流在地上,惊得他手中的瓜瓢也像是抹了润滑油,一下子从手里滑落。草儿的祖父心头瞬间咯噔一跳,头皮发麻,不寒而栗!猎人有猎人的规矩,草儿祖父为孩子立下的规矩,便是不能对着猎物连续开枪,面对猎物,优秀的猎人总是一枪击毙。但是这次,草儿的祖父听到了两声枪响,一股不祥的念头在他脑海翻滚,他知道,儿子跟自己一样,不会轻易连开两枪,除非,除非是那支老式猎枪走火……草儿的祖父什么也顾不上了,大步流星出了门,循着那枪响的方向走去。等他找到草儿的父亲的时候,草儿的父亲已经倒在一棵野山梅树下,躺在一片血泊里,没了呼吸。根据现场,草儿的祖父判断,百分百是枪走火了,那支从来都只指向猎物的枪,最终,也指向了他自己。眼泪,从老人的一只眼睛里流了下来,另一只却空荡荡的,几十年前,跟一头成年老熊搏斗的时候,他要了老熊的命,老熊却并不吃亏,抓瞎了他的这只眼睛,从此,他眼中的世界仿佛少了一半。
后来,草儿的父亲被葬在了那棵野山梅树下面。
原本,野山梅的花朵是白色的,那一年,那棵野山梅的花朵开成了猩红色,热烈,醒目,仿佛有着某种难以言喻的痛苦。如同遭遇了一场瘟疫,不只这一棵,山里的野山梅也全都开成了这样。
并且,野山梅是不结果的,这一年开始,野山梅结出了小小的青色果子来,摘一颗塞进嘴里,又苦又酸。
只有草儿的祖父知道,儿子这是死得不甘心哪,人虽然离开了,但他的灵魂却留了下来,传给了野山梅,他还在继续,他还在用力着,他通过它们,开花,结果,尽管眷恋、不甘心是如此明显。
偶尔,老早失去了爱人的祖父,告诉草儿:“这野山梅可不是普通的树哪,这树身上有你父亲的灵魂,有很多和你父亲一样的人的灵魂。”
七岁那年,草儿到了上学的年纪。学校在镇上,要走很远的路。读书山高路远,但这还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家里实在太穷,把房子倒过来也倒不出一分钱。遍山都是穷苦人,但他们却不愿意看到草儿辍学,力所能及地帮助着草儿完成学业。上大学的时候,草儿便脑袋削尖了似的打工、做兼职,为自己挣学费、生活费。毕业后,草儿放弃了城里的工作,回到家乡,在镇上初中做了一名教师。
在镇上教书,可草儿的心思还在山上,儿时住过的灰色木屋还在,艰难的生活记忆依然历历在目,祖父已经过世,但山上还有许多乡亲父老,他们还跟过去一样,很穷很穷。这是草儿心头的痛。然而,她毕竟只是个普普通通的教师,她唯一能做的,或者愿望,就是好好教书育人,帮助他们走出大山,走出穷困,走向美好的生活。
草儿喜欢她的学生,如同她喜欢山上的野山梅。为了学生,她起早贪黑,几乎用尽心思,然而,所有的期待就如同那些野山梅,尽管和许多果树有一样的春天,也开出了绚丽的花朵,可最终,结出的果子又酸又苦……
时间很快到了二〇〇八年。
这一年五月份,草儿的家乡遭遇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地震。地震当时,为了及时疏散班上的学生,草儿把自己留在了最后,就这样,一个美好善良的生命和灵魂,带着异常的坚定和无尽的遗憾,匆匆忙忙画上句号。
灾难很快过去,伤痛很快被遗忘。只是,不知哪一年,也不知道是谁,把山里的野山梅改良了,一棵棵种植在这大山的角角落落。
这些野山梅再也不是野山梅了,它们长成了另一种树,开出的花,不再猩红,是雪白的花,结出的果子,也不再又酸又苦,变得又酸又甜,乡亲父老们用这种果子酿出了可口的青梅酒。并且,这些野山梅,不再像它们的父辈那样慵懒麻木,要等到春天才开花,它们不畏严寒,冬天的时候就开了。
自此,野山梅开的花不再叫野山梅花了,人们只说梅花。
又过了好些年,当洁白无瑕的梅花开遍了草儿的那个村庄,草儿的家乡,当草儿的家乡以梅花和可口的青梅酒,吸引了远远近近无数的游客,草儿的那些学生,几乎忘记了世界上曾有草儿这样的老师,这样曾用生命为自己铺路、搭桥的人。也许,唯独在一个特别偶然的机缘下,于冬日里默默望着遍山盛开着的梅花,呼吸着那微弱却仍在用力的芬芳,其中定会有学生记起草儿,记起她在罹难之前,在生命最后留下的话:
“所有的人快跑。”
这些梅花,洁白无瑕的吻,仿佛,它们一直记得这句话。于是,脑海里缓缓浮现出一个寂寞和永久的灵魂。于是,人们带着某种无边的苦闷和焦虑,在一种混乱黏稠的背景中,持续用力。
鸡蛋的故事
在外婆家,我整天小野猫似的乱钻乱窜,洒落的影子无处不在。
“尿桶角角都是你!”大人们说。的确,除外婆家高高的房脊,黑咕隆咚的灶孔,再没有哪个角落会被忽略不曾造访。当然,也没有我干不出的事。
我闯进臭烘烘的鸡窝,把鸡撵得满天飞,歇到树上整天不敢下地,很快,报应就像装在潘多拉魔盒里的幽灵,而我亲自旋开了盖子:一身鸡虱子麻酥酥痒得我上蹿下跳,我屁股着了火似的哇哇大叫。为斩草除根,我跑到院里一口气把身上衣服脱光。外婆家在山上,我来不及上街找理发师把头上的草割掉,让虱子没有立足之地,外婆就拿来剪刀为我割草,最后,望着镜子里的光蛋,我哭了,哭的声音比夜里的星星还亮。
有年冬天,为了取暖,我把外婆家的草楼用火柴点燃,草楼被烧成骷髅。
还有一次,清明节,我在外公写着祖先们名字的纸钱上乱涂乱画,气得外公离家出走,在一棵桑树下面生了半天闷气……
外婆最疼我,疼我的外婆有一口白白的牙。
外婆那时很年轻,久不见的熟人相遇,都问她,这是你的啊?
外婆的脸就唰地红了,变成一个红苹果,她脑袋摇得像是拨浪鼓,一个劲儿解释说,我大女子的,不是我的。
外婆二十多岁开始生娃,一直生到快四十岁。四个女子,一个儿子。本来,舅舅头上还有一个男孩的,后来夭折了。据说,那个倒霉的舅舅,有天闹肚子疼,天黑吃了个煮鸡蛋,第二天再没有醒来。外婆和家里人不知流了多少眼泪。
外婆赶场总是要带上我。每次赶场,下山的时候我都变了一个人似的,斯斯文文贴在外婆身后,像她的一截尾巴。到了街上,我就鱼儿咬住鱼钩似的紧紧拽着我的外婆,开始一个劲儿地要这要那。一般情况下,外婆都会买吃的给我。偶尔,外婆故意似的把裤子荷包整个儿地掏出来,掏到外边,悄悄说,你看,哪里有钱?
然而,我其实早已看穿外婆的把戏。
我有的是策略,让亲爱的外婆掏钱满足我一连串的心愿。
我的策略就是亮着嗓门大声说出自己的那个心愿,总之,就像一个在为自己讨债的人那样,声音越大越好,人越多的地方越好。
每次,我外婆都会又惊又怕又像是不好意思似的,拉着我直奔要买的东西面前。
有的人,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疼,我亲爱的外婆就是如此。
一天,外婆又带我上街赶场。
我们走到街上,街上人已经多得寸步难行,人可真多啊,我敢肯定,人已经多到能把一个胖子挤成一个瘦子,把一个瘦子挤成一只虾子!到处人山人海,买东西的,卖东西的,看热闹的,脸生的,脸熟的。
好热闹!
我和亲爱的外婆优哉游哉穿行在这热闹的森林中。可是,我和外婆在街上没走几步远,一个老婆婆就迎面而来,走到外婆面前,欢喜地说了一声,嘿!
外婆一下子就认出是熟人,她也欢喜地回了一句,嘿!
每次,赶场外婆多少都会碰上熟人,一遇到熟人她就站在原地开始跟人家说长道短,把鸡毛蒜皮的事统统说上一遍,好像那些事不说出来就会生霉似的。我很烦这个,尤其是碰上那些年纪和外婆差不多大,甚至还老一点的女人,她们总是要说个没完!我就在肚子里抱怨,赶场就赶场,聊什么天,把我当成了什么!可是,外婆不这么想,跟她说话的人不这么想。她们痛痛快快聊天的时候,我只能老老实实站在一边,树桩一样,等她们把话说完。
外婆和那个老婆婆就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时而面对面,时而肩并肩,又从路中间,一直说到街边。街边全是卖菜的,那些山药、鸡蛋、大白菜、红薯、土豆、莴笋、蒜苗,长长地连成一串,比我外婆她们的话还长!
但是,那会儿我怎会晓得小心这些呢?后来我想。就在外婆她们说话那会儿,一个小男孩美滋滋舔着冰棍从我面前走了过去。我目送他走出很远,心里如同猫抓似的,很快,我又露出了一个不经意的微笑,我轻轻地问自己,人家哪里晓得我被他手里的冰棍勾引了呢?然后,我又轻轻地回答了我自己。
我于是很大声地告诉外婆,我要吃冰棍!
这句话我外婆一下子就听见了,那个老婆婆也听见了,我毫不怀疑,周围只要不是聋子都会听见的。
这句话,把我外婆她们的聊天一下子拦了下来。
可是,熟人面前,我亲爱的外婆态度很不明显,她没说给,也没说不给。她只是深深地看了我一眼,似乎希望我明白点什么,然后又继续跟那个老婆婆聊天。
外婆不理我!
我是不会放弃的!
我就站在外婆左边,大声喊,外婆我要吃冰棍!
我又站在外婆前面,大声喊,外婆我要吃冰棍!
可是我亲爱的外婆还是不理。可是,说她不理我呢,我站在左边喊的时候,外婆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挪到了她的右边;我站在前面喊的时候呢,外婆又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挪到她的后面!似乎都有些固执了!
所以,我和我外婆都忘记了身后,忘记了身后还有什么!
所以,当外婆把我拽向她身后的时候,我一下子失去了重心,扑通一声坐在地上。
直到这时,我还不晓得发生了什么!只觉得屁股上先是碎了似的,一阵乱响,然后,一种湿润的错误感觉涌起,贴到我的屁股上,凉丝丝的。怎么回事?但是,最主要的,我还是想着我的冰棍,并且,这似乎也是最好的机会。当我正准备拖着哭腔,坐在地上向我外婆大声喊出自己的心愿,背后却忽然传来一声怒吼,我的妈呀,我的天,我的地哦,你这个娃儿,长个眼睛嘛,我的鸡蛋都让你坐烂啦!快起来!
说得好像我没长眼睛一样!
我回头一看,一个中年妇女正满面愁云试着把我推开。
我一下子从地上站起来。
天,我居然不小心坐在别人卖的鸡蛋上面啦!
难怪屁股不舒服!
那些鸡蛋是装在一个蛇皮口袋里面的,显得十分原生态。只是,坏了好多个的样子。那些坏了的鸡蛋,黄灿灿的一片,从口袋里流出来。起来的时候,我还从屁股上摘了一个,好像它是我下的似的,我惊呆了。我想,我怎么会要别人的鸡蛋呢?我就把那个鸡蛋,一把扔进了那蛇皮口袋里!
这时候,中年妇女冒火连天地冲我外婆吼了一句什么。
然后,我看见外婆二话没说,一下子蹲在地上,蹲在那堆鸡蛋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