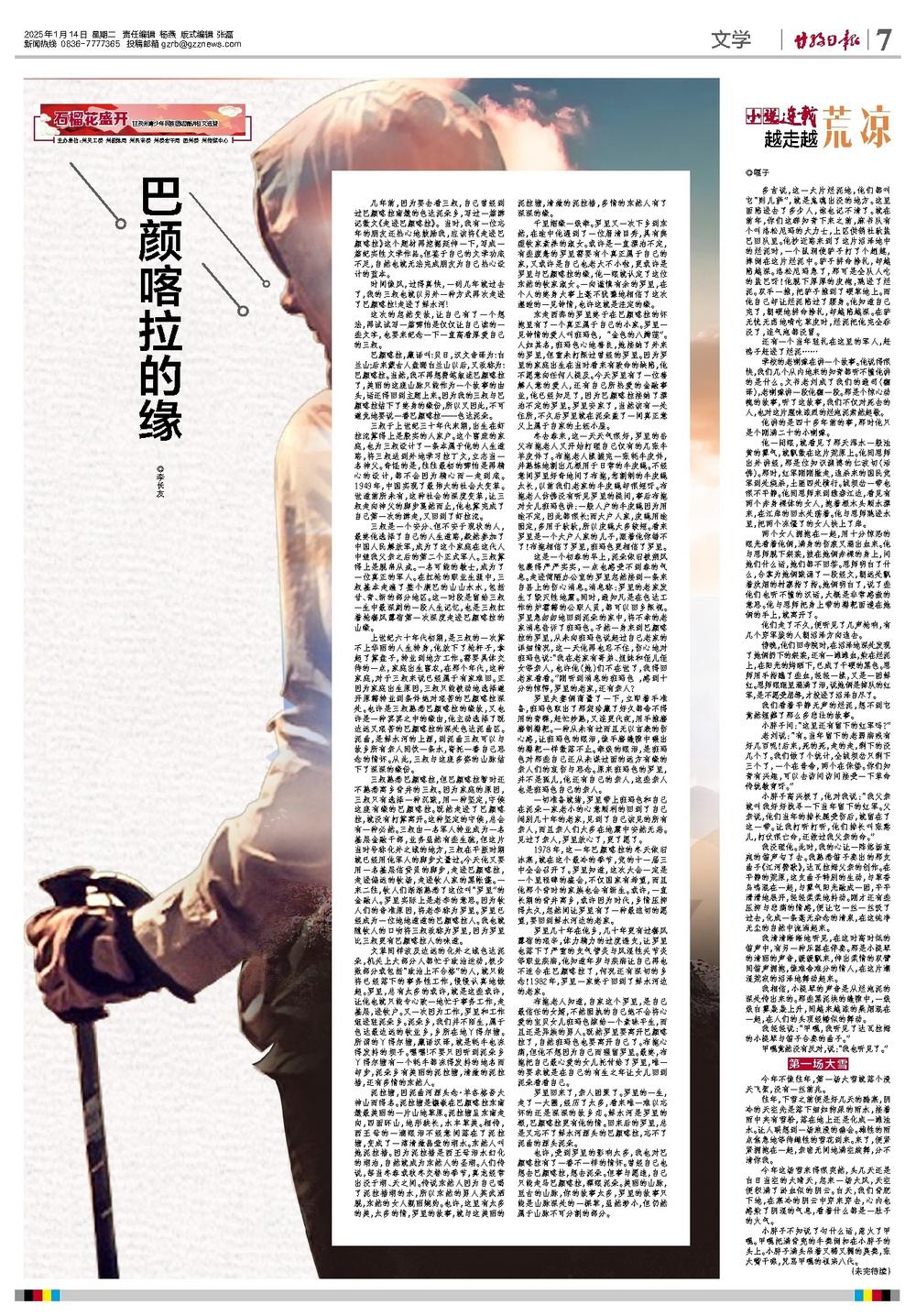◎李长友
几年前,因为要去看三叔,自己曾经到过巴颜喀拉南麓的色达泥朵乡,写过一篇游记散文《走进巴颜喀拉》。 当时,我有一位忘年的朋友还热心地鼓励我,应该将《走进巴颜喀拉》这个题材再挖掘延伸一下,写成一篇纪实性文学作品。但鉴于自己的文学功底不足,自然也就无法完成朋友为自己热心设计的蓝本。
时间像风,过得真快,一刮几年就过去了,我的三叔也就以另外一种方式再次走进了巴颜喀拉!走进了鲜水河!
这次的忽然变故,让自己有了一个想法,再试试写一篇哪怕是仅仅让自己读的一些文字,也要来纪念一下一直高看厚爱自己的三叔。
巴颜喀拉,藏语叫:贝日,汉文音译为:白兰山;后来蒙古人盘踞白兰山以后,又改称为:巴颜喀拉。当然,我不再想费笔叙述巴颜喀拉了,美丽的这座山脉只能作为一个故事的由头,话还得回到主题上来。因为我的三叔与巴颜喀拉结下了终身的缘份,所以又因此,不可避免地要说一番巴颜喀拉——色达泥朵。
三叔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末期,出生在虾拉沱算得上是殷实的人家户。这个富庶的家庭,也为三叔设计了一条本属于他的人生道路,将三叔送到外地学习拉丁文,立志当一名神父。奇怪的是,往往最初的哪怕是再精心的设计,都不会因为精心而一走到底。1949年,中国实现了最伟大的社会大变革。世道前所未有,这种社会的深度变革,让三叔走向神父的脚步戛然而止,他也算完成了自己第一次的游走,又回到了虾拉沱。
三叔是一个安分、但不安于现状的人,最终他选择了自己的人生道路,毅然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了这个家庭在这代人中继我父亲之后的第二个正式军人。三叔算得上是脱帛从戎。一名可能的教士,成为了一位真正的军人。在扛枪的职业生涯中,三叔基本走遍了整个康巴的山山水水,包括甘、青、新的部分地区。这一时段是留给三叔一生中最深刻的一段人生记忆,也是三叔扛着枪餐风露宿第一次深度走进巴颜喀拉的山缘。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是三叔的一次算不上华丽的人生转身,他放下了枪杆子,拿起了算盘子,转业到地方工作。需要具体交待的一点,家庭出生富农,在那个年代,这种家庭,对于三叔来说已经属于有家难回。正因为家庭出生原因,三叔只能被动地选择避开原籍转业到条件绝对艰苦的巴颜喀拉深处。也许是三叔熟悉巴颜喀拉的缘故,又也许是一种冥冥之中的缘由,他主动选择了既边远又艰苦的巴颜喀拉的深处色达泥曲区。泥曲,是鲜水河的上源,到泥曲三叔可以与故乡所有亲人同饮一条水,寄托一番自己思念的情怀。从此,三叔与这座多姿的山脉结下了深深的缘份。
三叔熟悉巴颜喀拉,但巴颜喀拉暂时还不熟悉离乡背井的三叔。因为家庭的原因,三叔只有选择一种沉默,用一种坚定,守候这座有缘的巴颜喀拉。既然走进了巴颜喀拉,就没有打算离开。这种坚定的守候,总会有一种必然。三叔由一名军人转业成为一名基层金融干部,业务虽然有些生疏,但这片当时号称化外之域的地方,三叔在平叛时期就已经用他军人的脚步丈量过。今天他又要用一名基层信贷员的脚步,走进巴颜喀拉,走进偏远的牧场,走进牧人家的黑帐篷。一来二往,牧人们渐渐熟悉了这位叫“罗里”的金融人。罗里实际上是老李的意思。因为牧人们的音准原因,将老李称为罗里。罗里已经成为一位地地道道的巴颜喀拉人。我也就随牧人的口吻将三叔改称为罗里,因为罗里比三叔更有巴颜喀拉人的味道。
文革同样波及边远的化外之域色达泥朵,机关上大部分人都忙于政治运动,极少数部分或包括“政治上不合格”的人,就只能将已经落下的事务性工作,慢慢认真地做起。罗里,总有太多的或许,就是这些或许,让他也就只能专心致一地忙于事务工作,走基层,进牧户。又一次因为工作,罗里和工作组进驻泥朵乡。泥朵乡,我们并不陌生,属于色达最边远的牧业乡,乡所在地丫得尔塘。所谓的丫得尔塘,藏语汉译,就是牦牛也冻得发抖的坝子。嘿嘿!不要只因听到泥朵乡丫得尔塘有一个牦牛都冻得发抖的地名而却步,泥朵乡有美丽的泥拉塘,清澈的泥拉措,还有多情的东然人。
泥拉塘,因泥曲河源头念·羊各格吾大神山而得名。泥拉塘是镶嵌在巴颜喀拉东南麓最美丽的一片山地草原。泥拉塘呈东南走向,四面环山,地形狭长,水丰草美。相传,西王母的一滴眼泪不经意间落在了泥拉塘,变成了一湾清澈晶莹的湖水。东然人叫她泥拉措。因为泥拉措是西王母泪水幻化的湖泊,自然就成为东然人的圣湖。人们传说,每当冬春或秋冬交替的季节,真龙经常出没于湖、天之间。传说东然人因为自己喝了泥拉措湖的水,所以东然的男人英武洒脱,东然的女人靓丽婉约。也许,这里有太多的美,太多的情,罗里的故事,就与这美丽的泥拉塘,清澈的泥拉措,多情的东然人有了深深的缘。
千里姻缘一线牵。罗里又一次下乡到东然,在途中他遇到了一位眉清目秀,具有典型牧家素养的淑女。或许是一直漂泊不定,有些疲惫的罗里需要有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又或许是自己也老大不小啦,更或许是罗里与巴颜喀拉的缘,他一眼就认定了这位东然的牧家淑女。一向谨慎有余的罗里,在个人的终身大事上毫不犹豫地相信了这次邂逅的一见钟情,也许这就是注定的缘。
东走西奔的罗里终于在巴颜喀拉的怀抱里有了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小家。罗里一见钟情的爱人叫班玛色, “金色的八瓣莲”。人如其名,班玛色心地善良,她接纳了外来的罗里,但重未打探过曾经的罗里。因为罗里的家庭出生在当时看来有致命的缺陷,他不愿意向任何人提及。今天罗里有了一位善解人意的爱人,还有自己所热爱的金融事业,他已经知足了,因为巴颜喀拉接纳了漂泊不定的罗里。罗里安家了,当然该有一处住所,不久后罗里就在泥朵盖了一间真正意义上属于自家的土坯小屋。
冬去春来,这一天天气很好,罗里的岳父布拖老人又开始打理自己仅有的几张牛羊皮件了。布拖老人揉搓完一张牦牛皮件,并熟练地割出几根用于日常的牛皮绳。不经意间罗里好奇地问了布拖,您割制的牛皮绳太长,以前我们老家的牛皮绳却很短呀。布拖老人仿佛没有听见罗里的提问,事后布拖对女儿班玛色讲:一般人户的牛皮绳因为用途不定,因此都很长;而大户人家,皮绳用途固定,多用于驮驮,所以皮绳大多较短。看来罗里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儿子,跟着他你错不了!布拖相信了罗里,班玛色更相信了罗里。
这是一个初春的早上,泥朵依旧被朔风包裹得严严实实,一点也感受不到春的气息。走进简陋办公室的罗里忽然接到一条来自县上的伤心消息。消息称:罗里的老家发生了毁灭性地震。同时,通知凡是在色达工作的炉霍籍的公职人员,都可以回乡探视。罗里急匆匆地回到泥朵的家中,将不幸的老家消息告诉了班玛色。孑然一身来到巴颜喀拉的罗里,从未向班玛色说起过自己老家的详细情况,这一天他再也忍不住,伤心地对班玛色说:“我在老家有哥弟、姐妹和侄儿侄女等亲人,也许他(她)们不在世了,我得回老家看看。”刚听到消息的班玛色 ,感到十分的惊愕,罗里的老家,还有亲人?
罗里夫妻俩商量了一下,立即着手准备,班玛色取出了那袋珍藏了好久都舍不得用的青稞,赶忙炒熟,又连更代夜,用手推磨磨制糌粑。一种从未有过而且无以言表的伤心感,让班玛色的眼泪,像手磨缝隙中碾出的糌粑一样散落不止。牵线的眼泪,是班玛色对那些自己还从未谋过面的远方有缘的亲人们的哀伤与思念。原来班玛色的罗里,并不是孤儿,他还有自己的亲人,这些亲人也是班玛色自己的亲人。
一切准备就绪,罗里带上班玛色和自己在泥朵一家老小的心意顺利的回到了自己阔别几十年的老家,见到了自己该见的所有亲人,而且亲人们大多在地震中安然无恙。见过了亲人,罗里放心了,更了愿了。
1978年,这一年巴颜喀拉的冬天依旧冰寒,就在这个最冷的季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罗里知道,这次大会一定是一个里程碑的盛会,不仅国家有希望,而且他那个背时的家族也会有新生。或许,一直长期的背井离乡,或许因为时代,乡情压抑得太久,忽然间让罗里有了一种最迫切的愿望,要回到鲜水河边的老家。
罗里几十年在他乡,几十年更有过餐风露宿的艰辛,体力精力的过度透支,让罗里也落下了严重的支气管炎与风湿性关节炎等职业疾病,他知道年岁与疾病让自己再也不适合在巴颜喀拉了,何况还有深切的乡念!1982年,罗里一家终于回到了鲜水河边的老家。
布拖老人知道,自家这个罗里,是自己最信任的女婿,不然固执的自己绝不会将心爱的宝贝女儿班玛色嫁给一个素昧平生,而且还是异族的男人。既然罗里要离开巴颜喀拉了,自然班玛色也要离开自己了。布拖心痛,但他不想因为自己而强留罗里。最终,布拖把自己最心爱的女儿托付给了罗里,唯一的要求就是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让女儿回到泥朵看看自己。
罗里回来了,亲人团聚了。罗里的一生,走了一大圈,经历了太多,看来唯一难以忘怀的还是深深的故乡恋。鲜水河是罗里的根,巴颜喀拉更有他的情。回来后的罗里,总是又忘不了鲜水河源头的巴颜喀拉,忘不了泥曲的源头泥朵。
也许,受到罗里的影响太多,我也对巴颜喀拉有了一番不一样的情怀。曾经自己也想去巴颜喀拉,想去泥朵。但事与愿违,自己只能走马巴颜喀拉,瞟眼泥朵。美丽的山脉,亘古的山脉,你的故事太多,罗里的故事只能是山脉深处的一棵草,虽然渺小,但仍然属于山脉不可分割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