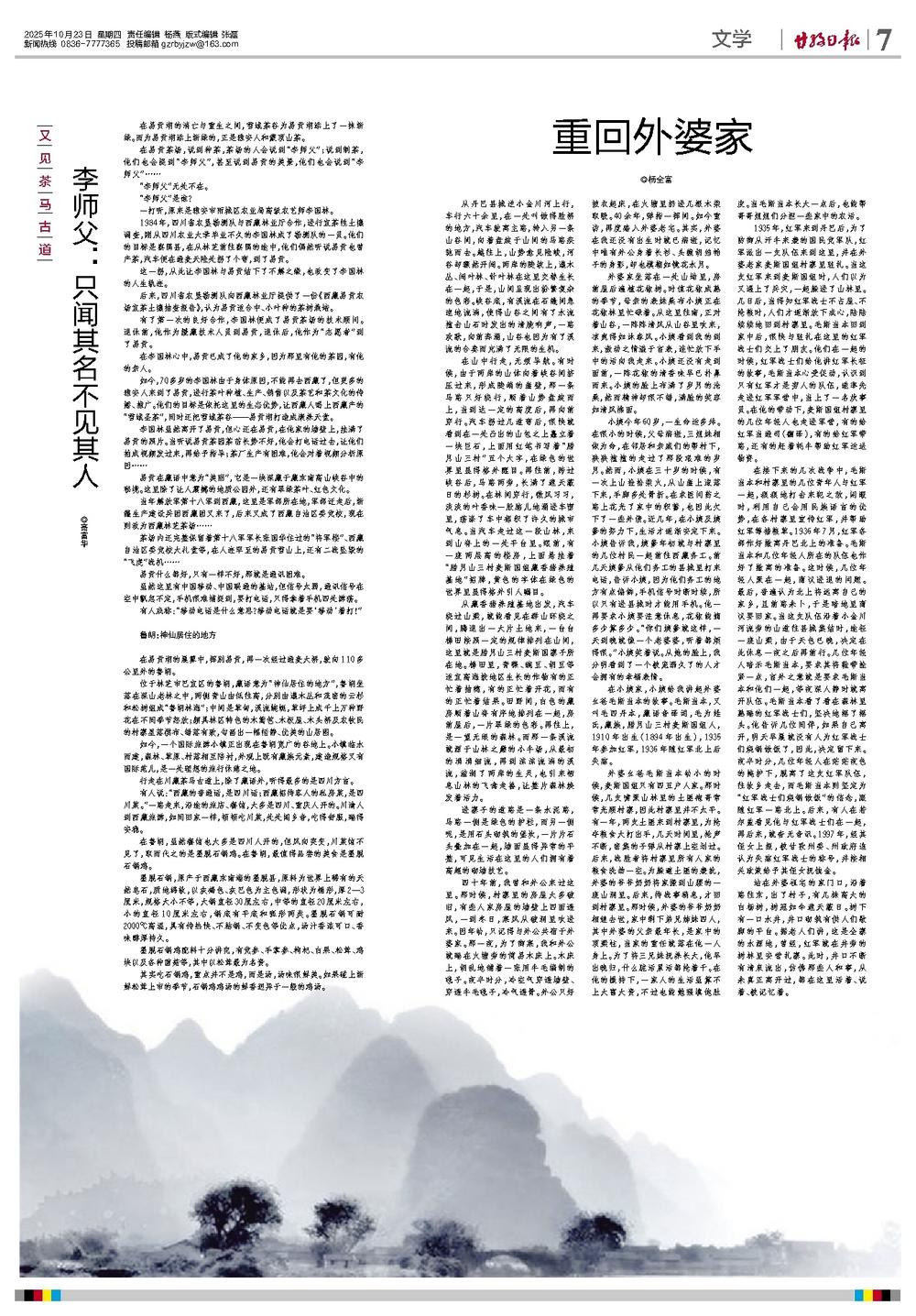◎杨全富
从丹巴县城逆小金川河上行,车行六十余里,在一处叫做得胜桥的地方,汽车驶离主路,转入另一条山谷间,向着盘旋于山间的马路疾驰而去。越往上,山势愈见险峻,河谷却骤然开阔。两岸的陡坡上,灌木丛、阔叶林、针叶林在这里交替生长在一起,于是,山间呈现出纷繁复杂的色彩。峡谷底,有溪流在石缝间急速地流淌,使得山谷之间有了水流撞击山石时发出的清脆响声,一路欢歌,向前奔涌,山谷也因为有了溪流的合奏而充满了无限的生机。
在山中行走,无须导航。有时候,由于两岸的山体向着峡谷间挤压过来,形成陡峭的崖壁,那一条马路只好绕行,顺着山势盘旋而上,当到达一定的高度后,再向前穿行。汽车拐过几道弯后,很快就看到在一处凸出的山包之上矗立着一块巨石,上面用红笔书写着“腊月山三村”五个大字,在绿色的世界里显得格外醒目。再往前,跨过峡谷后,马路两旁,长满了遮天蔽日的杉树。在林间穿行,微风习习,淡淡的叶香味一股脑儿地涌进车窗里,荡涤了车中郁积了许久的城市气息。当汽车走过这一段山林,来到山脊上的一处平台里。眼前,有一座两层高的楼房,上面悬挂着“腊月山三村麦斯国组藏香猪养殖基地”招牌,黄色的字体在绿色的世界里显得格外引人瞩目。
从藏香猪养殖基地出发,汽车绕过山梁,就能看见在群山环绕之间,腾退出一大片土地来,一台台梯田按照一定的规律排列在山间,这里就是腊月山三村麦斯国寨子所在地。梯田里,青稞、豌豆、胡豆等适宜高海拔地区生长的作物有的正忙着抽穗,有的正忙着开花,而有的正忙着结果。田野间,白色的藏房顺着山脊有序地排列在一起,房前屋后,一片翠绿的色彩。再往上,是一望无垠的森林。而那一条溪流就源于山林之巅的小牛场,从最初的涓涓细流,再到淙淙流淌的溪流,滋润了两岸的生灵,也引来栖息山林的飞禽走兽,让整片森林焕发着活力。
进寨子的道路是一条水泥路,马路一侧是绿色的护栏,而另一侧呢,是用石头砌筑的堡坎,一片片石头叠加在一起,墙面显得异常的平整,可见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拥有着高超的砌墙技艺。
四十年前,我曾和外公来过这里。那时候,村寨里的房屋大多破旧,有些人家房屋的墙壁上四面透风,一到冬日,寒风从破洞里吹进来。因年幼,只记得与外公共宿于外婆家。那一夜,为了御寒,我和外公就睡在火塘旁的简易木床上。木床上,胡乱地铺着一张用牛毛编制的毯子。夜半时分,冷空气穿透墙壁、穿透牛毛毯子,冷气透骨。外公只好披衣起床,在火塘里扔进几根木柴取暖。40余年,弹指一挥间。如今重访,再度踏入外婆老宅。其实,外婆在我还没有出生时就已病逝,记忆中唯有外公身着长衫、头缠胡绉帕子的身影,却也模糊如镜花水月。
外婆家坐落在一处山坳里,房前屋后遍植花椒树。时值花椒成熟的季节,母亲的表妹桑布小姨正在花椒林里忙碌着。从这里往南,正对着山谷,一阵阵清风从山谷里吹来,凉爽得如沐春风。小姨看到我的到来,激动之情溢于言表,连忙放下手中的活向我走来。小姨还没有走到面前,一阵花椒的清香味早已扑鼻而来。小姨的脸上布满了岁月的沧桑,然而精神却很不错,满脸的笑容如清风拂面。
小姨今年60岁,一生命运多舛。在很小的时候,父母病逝,三姐妹相依为命,在邻居和亲戚们的帮村下,跌跌撞撞的走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然而,小姨在三十岁的时候,有一次上山捡拾柴火,从山崖上滚落下来,手脚多处骨折。在求医问药之路上花光了家中的积蓄,也因此欠下了一些外债。近几年,在小姨及姨爹的努力下,生活才逐渐安定下来。小姨告诉我,姨爹年初就与村寨里的几位村民一起前往西藏务工。前几天姨爹从他们务工的县城里打来电话,告诉小姨,因为他们务工的地方有点偏僻,手机信号时断时续,所以只有进县城时才能用手机。他一再要求小姨要注意休息,花椒能摘多少算多少。“你们姨爹就这样,一天到晚就像一个老婆婆,听着都烦得很。”小姨笑着说。从她的脸上,我分明看到了一个被宠溺久了的人才会拥有的幸福表情。
在小姨家,小姨给我讲起外婆幺爸毛斯当本的故事。毛斯当本,又叫毛四丹本,藏语音译词,毛为姓氏,藏族,腊月山三村麦斯国组人,1910年出生(1894年出生),1935年参加红军,1936年随红军北上后失踪。
外婆幺爸毛斯当本幼小的时候,麦斯国组只有四五户人家。那时候,几支啸聚山林里的土匪袍哥常常光顾村寨,因此村寨里并不太平。有一年,两支土匪来到村寨里,为抢夺粮食大打出手,几天时间里,枪声不断,密集的子弹从村寨上空划过。后来,战胜者将村寨里所有人家的粮食洗劫一空。为躲避土匪的袭扰,外婆的爷爷奶奶将家搬到山腰的一座山洞里。后来,待战事稍息,才回到村寨里。那时候,外婆的爷爷奶奶相继去世,家中剩下弟兄姊妹四人,其中外婆的父亲最年长,是家中的顶梁柱,当家的重任就落在他一人身上。为了将三兄妹抚养长大,他早出晚归,什么脏活累活都抢着干。在他的操持下,一家人的生活虽算不上大富大贵,不过也能勉强填饱肚皮。当毛斯当本长大一点后,也能帮哥哥姐姐们分担一些家中的农活。
1935年,红军来到丹巴后,为了防御从汗牛来袭的国民党军队,红军派出一支队伍来到这里,并在外婆老家麦斯国组村寨里驻扎。当这支红军来到麦斯国组时,人们以为又遇上了兵灾,一起躲进了山林里。几日后,当得知红军战士不占屋、不抢粮时,人们才逐渐放下戒心,陆陆续续地回到村寨里。毛斯当本回到家中后,很快与驻扎在这里的红军战士们交上了朋友。他们在一起的时候,红军战士们给他讲红军长征的故事,毛斯当本心受促动,认识到只有红军才是穷人的队伍,遂率先走进红军军营中,当上了一名炊事员。在他的带动下,麦斯国组村寨里的几位年轻人也走进军营,有的给红军当通司(翻译),有的给红军带路,还有的赶着牦牛帮助红军运送物资。
在接下来的几次战争中,毛斯当本和村寨里的几位青年人与红军一起,狠狠地打击来犯之敌,闲暇时,利用自己会用民族语言的优势,在各村寨里宣传红军,并帮助红军筹措粮草。1936年7月,红军各部作好撤离丹巴北上的准备。毛斯当本和几位年轻人所在的队伍也作好了撤离的准备。这时候,几位年轻人聚在一起,商议进退的问题。最后,普遍认为北上将远离自己的家乡,且前路未卜,于是暗地里商议要回家。当这支队伍沿着小金川河流旁的山道往县城集结时,途径一座山梁,由于天色已晚,决定在此休息一夜之后再前行。几位年轻人暗示毛斯当本,要求其将鞋带拴紧一点,言外之意就是要求毛斯当本和他们一起,等夜深人静时就离开队伍。毛斯当本看了看在森林里熟睡的红军战士们,坚决地摇了摇头。他告诉几位同伴,如果自己离开,明天早晨就没有人为红军战士们烧锅做饭了,因此,决定留下来。夜半时分,几位年轻人在茫茫夜色的掩护下,脱离了这支红军队伍,往故乡走去,而毛斯当本则坚定为“红军战士们烧锅做饭”的信念,跟随红军一路北上。后来,有人在若尔盖看见他与红军战士们在一起,再后来,就杳无音讯。1997年,经其侄女上报,被甘孜州委、州政府追认为失踪红军战士的称号,并按相关政策给予其侄女抚恤金。
站在外婆祖宅的家门口,沿着路往东,出了村子,有几株高大的白杨树,树冠如伞遮天蔽日。树下有一口水井,井口砌筑有供人们歇脚的平台。据老人们讲,这是全寨的水源地,曾经,红军就在井旁的树林里安营扎寨。此时,井口不断有清泉流出,仿佛那些人和事,从未真正离开过,都在这里活着、说着、被记忆着。